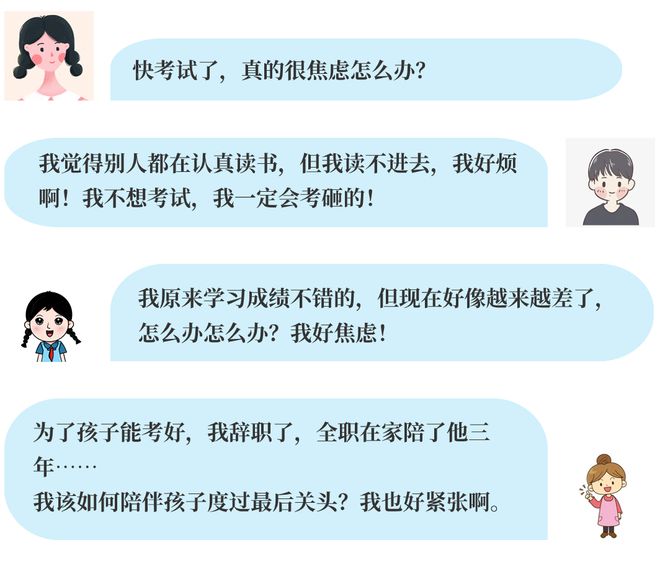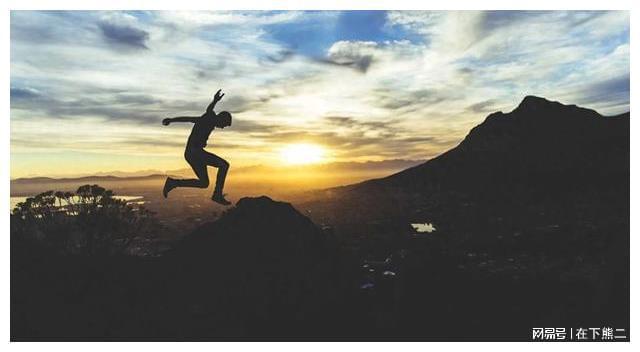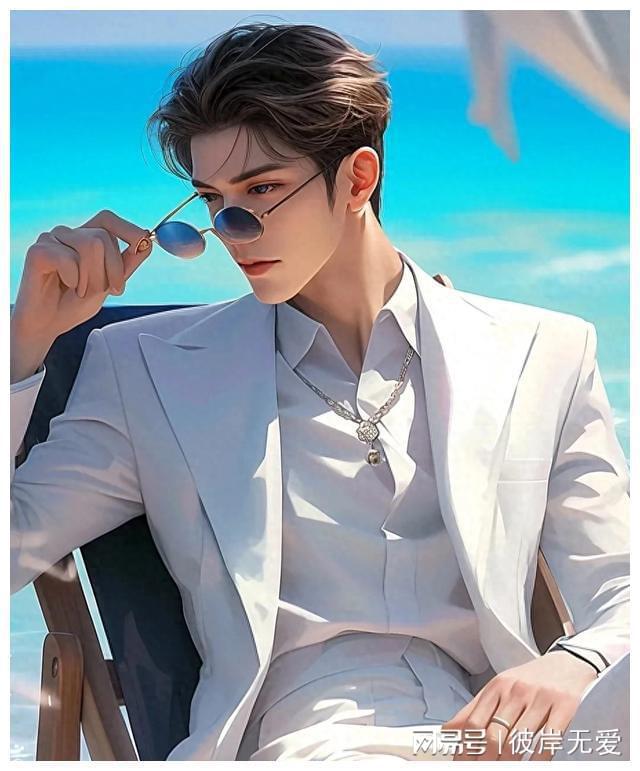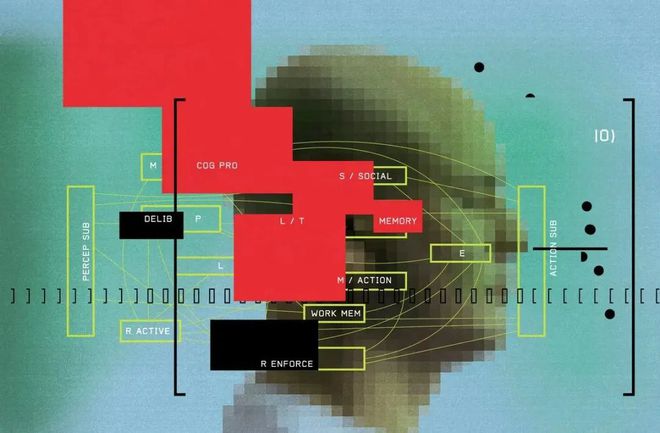消极偏差还是积极缺乏:抑郁的积极心理学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2010, Vol. 18, No. 4, 590–59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消极偏差还是积极缺乏:抑郁的积极心理学解释
周雅1, 2 刘翔平1, 2 苏洋1 冉俐雯1
(1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摘要:抑郁的认知理论被认为是当代最具影响的抑郁理论之一, 其中贝克抑郁理论与无望抑郁理论是两大主要的认知理论。认知理论主张消极认知偏差是导致抑郁的易感因素。然而, “抑郁现实主义” 及“积极错觉”等研究却证实抑郁个体并不存在消极认知偏差。以往研究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心理学过分关注消极的病理化倾向。新兴的积极心理学则试图从全新视角解释抑郁, 导致抑郁的原因不是个体身上积极因素的缺位, 而是积极力量未被充分发挥。
关键词:抑郁症; 抑郁认知模型; 抑郁现实主义; 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治疗
分类号R395
1 背景
抑郁障碍(depression disorders), 即抑郁症,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TR) 将其定义为一种“ 情感障碍”(affective disorders), 其在临床上最为显著的表现为情绪低落、精力减退、活动降低, 以及愉快感与兴趣感的丧失, 重度抑郁甚至导致心理迟滞与思维困难。抑郁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 最近研究显示, 至少1700 万的美国成年人在一年中曾经历过抑郁, 即每10 个成年人中就有1 个人有过抑郁体验, 每5 个家庭中就有1 个家庭受到抑郁困扰(引自美国医学会, 2008) 。现实情形不仅相当严峻, 而且正在逐渐恶化。二战之后, 抑郁的发生率在代际间呈现上升趋势(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而据世界卫生组织2004 年的调查(引自任俊, 2006), 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 抑郁人数也比20 世纪中叶至少增加1 倍。世界卫生组织甚至预测, 到2020 年, 在世界范围内, 抑郁将会成为致使成年阶段残障或死亡的除心脏病外的最大原因。此外, 抑郁发作的平均年龄呈现下降趋势, 青少年阶段抑郁的发生率急剧上升。研究估计, 美国青少年中15%~20% 患有重度抑郁(Lewinsohn & Essau, 2002); 而在我国约有42.3% 的中学生存在轻度抑郁(冯正直, 张大均, 2005) 。
面对这一现状, 我们不禁疑惑:现在的人类相比过去的人类, 拥有极大丰富的物质以及更加发达的文明, 人类理应更加幸福; 我们的心理学, 作为一门致力追求人类幸福的科学, 相比过去, 已建构了更加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广泛深厚的专业基础, 在诸多领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著有贡献, 心理学家至少能对14 种50 年前无能为力的心理疾病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然而, 人类始终无法摆脱抑郁。心理学家(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将这一现象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困惑”。
2 抑郁的传统理论
抑郁究竟因何产生?现代有关抑郁的思想, 最早源于早期精神分析学派建立起的抑郁病源学说。而当代在对抑郁产生机制的研究中, 较为公认的病因模型为抑郁的“ 素质— 应激模型” (Diathesis-Stress Model) 。Monroe 和Simons (1991) 将这个60 年代精神分裂症领域的概念模型用于解释抑郁的产生机制, 指出导致抑郁的两个基本因素包括:消极的生活事件和个体的易感因素。消极的生活事件, 即应激源, 这些事件一般使得个体失去依恋、安全、自我认同或是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素质作为个体对于抑郁的易感因素, 则影响着消极事件可能对个体造成的伤害。众多研究表明, 经历同样的消极事件, 并非所有个体都会产生抑郁, 抑郁只会侵袭那些更为敏感、脆弱的个体。究竟哪些个体变量构成了抑郁的“素质”, 这一问题成为当代抑郁研究的关键。有关抑郁的各种理论, 其差异主要在于对“素质”的不同界定。在这其中, 作为目前影响最为广泛的抑郁理论, 抑郁的认知理论将“素质”解释为个体消极的认知偏向。
2.1 抑郁的消极认知偏差
抑郁的认知理论着重考察认知变量在抑郁中的作用, 这些理论认为, 个体在信息加工、期望归因以及自我评价等各认知水平上的消极偏向是导致抑郁的高危因素。贝克抑郁理论与无望抑郁理论, 是两大主要的抑郁认知理论。
2.1.1 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
贝克(Aron T. Beck) 作为最先倡导抑郁认知理论的心理学家之一, 提出认知成分及认知过程是抑郁的易感因素。贝克的抑郁认知模型(Beck & Weishaar, 2000) 包含两个层次(见图1), 即深层的功能失调信念(dysfunctional beliefs) 和表层的消极自动思维(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二者通过消极图式的激活以及歪曲的认知加工联系起来。其中, 功能失调信念作为一种抑郁素质, 反映的是个体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僵化、极端的态度, 它源自童年早期的消极经验, 外界的评价与条件性价值经由内化, 构成个体消极的自我图式(depressogenic/negative schemas) 。这些潜在的消极图式一般不被察觉, 但是一经消极事件激活, 便会制造出大量的消极自动思维, 抑郁体验随之而来。贝克认为, 抑郁个体的消极图式使得他们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具有歪曲错误、不合逻辑的认知偏向, 也被称为系统偏差(systematic errors), 这些认知偏差包括灾难化、专断化、以偏概全以及非黑即白等。

贝克尤其强调三类导致抑郁的消极认知:(1) 没有希望、生活没有期待。贝克将这三类观念称对自我的消极看法, 即抑郁个体总倾向于自我贬为“消极认知三联组”(negative cognitive triad), 并低、自我谴责; (2) 对世界的消极看法, 即抑郁个认为抑郁的其他特征, 诸如躯体症状、动机障碍, 体总是不满足于生活现状, 认为整个世界对自己以及情感失调, 都是对这些消极认知的反应。不公、与自己为难; (3) 对未来的消极看法, 即抑2.1.2 无望抑郁的认知模型郁个体总对自己的能力抱有悲观态度, 认为成功无望抑郁(hopeless depression) 的认知理论源于习得无助现象的研究。基于习得无助的归因理论, Abramson 等人(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吸收贝克的某些理念, 提出无望抑郁的模型(见图2), 其中, 消极归因风格作为抑郁的素质。当消极生活事件发生时, 具有消极归因风格的个体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解释事件, 认为事件的原因是稳定的、普遍的, 这种觉知将会导致无望体验。无望体验使得个体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不利处境, 因而陷入无望抑郁。无望抑郁被认为是抑郁的一种亚类型。如果个体将稳定、普遍的消极事件同时归为内部的原因, 低自尊便会伴随抑郁出现。值得注意的是, 贝克将与自我有关的消极认知作为所有类型抑郁的主要特征, 而Abramson 等(1989)则坚持认为与自我有关的消极认知仅存在于某些类型的抑郁。
2.2 消极认知偏差的反证
抑郁认知理论关于抑郁个体存在消极认知偏向的观点已经得到众多研究支持。然而, 也有研究结果对其提出质疑。
2.2.1 认知易感因素存在吗?
在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中, “功能失调信念” 在应激事件的刺激下导致个体消极的认知偏差, 从而产生抑郁。即使抑郁的体验或症状暂时消失, 功能失调信念作为抑郁的素质, 仍根植于个体的认知图式之中, 它是一种稳定的认知结构。不少研究都曾试图证明这种认知结构的存在, 然而结果却不尽理想。虽然处于抑郁中的个体确实要比非抑郁的个体具有更多功能失调的信念, 但是, 一旦抑郁消失, 二者在功能失调信念量表上的得分便不再有显著差异(e.g., Ingram, 2005)。可以就此推论, 功能失调信念可能只是伴随抑郁存在的一种症状, 而并不是抑郁产生的真正原因。消极认知偏向也许会出现在抑郁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抑郁个体本身必然具有某种持续的、稳定的认知层面的消极特质。
无独有偶, 对于无望抑郁理论所提出的抑郁易感因素在于消极归因风格, 也有研究对此予以否认。Follette 和Jacobson (1987)考察了大学生的归因风格与考试失败之后抑郁情绪变化的关系, 结果发现, 归因风格与抑郁情绪变化之间相关不高, 而获知考试失败后的即时归因与抑郁情绪变化之间却明显相关。这一结果提供了另外的解释可能— 与其说悲观归因风格导致抑郁, 不如说抑郁中的消极情绪损害认知从而形成归因偏差。此外, 作为抑郁消极归因理论的倡导者, Abramson 等人(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自己也承认, “我们不得不清楚地区分三个概念, 即引发症状的必要因素(necessary causes)、充分因素(sufficient causes) 以及贡献因素(contributory causes)”。其中, 必要因素是某种病理机制的核心所在, 缺乏这些因素, 疾病一定不会产生, 但是具备这些因素, 疾病并不一定产生, 在这个意义上, “必要因素”正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易感因素”; 而充分因素则只是某种疾病的伴随性表现, 疾病症状的发生必须要求这些因素的存在, 症状一旦消退, 这些因素可能也就不复存在; 贡献因素在病理机制中地位最为微弱, 这些因素仅仅只是增加症状出现的风险, 对于疾病的产生既不必要也不充分。至于“消极的归因风格, 可能只是导致抑郁的充分因素而已”(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抑郁个体的认知归因并非必定具有功能系统上的绝对消极的偏差。
2.2.2 抑郁原是“现实主义”
对抑郁认知理论构成直接冲击的证据, 发端于Alloy 和Abramson (1979)有关抑郁个体控制能力的研究。根据抑郁个体可能因自我贬低而低估自己对事件的控制能力的假设, 她们设计了如下的实验程序:在有些条件下, 被试按钮可以控制灯是否变亮, 在另些条件下, 被试按钮则与灯是否变亮完全无关, 最后要求被试判断自己按钮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灯的变亮。研究结果却是出乎意料, 抑郁被试并未低估自己的控制能力, 他们恰恰能够客观地、正确地做出判断; 反倒正常被试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 表现出某种过分积极的认知偏差。自此之后, 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认知偏向这一概念— 究竟是抑郁者更加消极, 还是正常人太过积极?
后续研究不断表明, 抑郁个体并不是绝对地消极。抑郁个体并不总是自我贬低, 相反, 他们经常会表现出自我赞美; 在自我概念的某些方面, 他们甚至会比正常人更加积极地看待自己(e.g., Pelham, 1993)。在自我评价任务上, 抑郁被试也许显得要比正常被试消极, 但是抑郁个体的这种判断可能更加符合现实、更加客观准确(e.g., Campbell & Fehr, 1990)。基于这些证据, 心理学家Mischel(引自乔纳森.布朗, 2004)创造出这样的术语—“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 意即抑郁者并不存在过分消极的认知偏向, 他们只是对于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对于现实的风险与损失具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面对诸多反证, 抑郁认知理论的主张者也不得不调整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抑郁现实主义”。贝克(Haaga & Beck, 1995)表示, “情绪的痛苦与认知准确性之间也许是一种曲线的关系:没有抑郁的心理健康的个体具有积极的认知偏向; 轻度抑郁的个体是‘现实主义’的, 有着比较客观的态度与信念; 而那些极为严重的抑郁患者应该还是存在消极认知偏向的”。有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 证明抑郁的消极认知偏向与抑郁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联系(e.g., McKendree-Smith & Scogin, 2000)。
3 抑郁的“积极”阐释
综上所述, 抑郁认知理论关于消极认知偏差导致抑郁的主张并不确定成立。抑郁个体, 尤其那些并非极度严重的抑郁个体, 对于自我以及现实的认知很可能比正常人更为客观、准确。果真如此的话, 抑郁又是从何而来?
3.1 积极心理理念
回顾抑郁的认知理论, 其关注的核心在于个体认知的消极偏向。实际上, 这种内容建构与价值导向本身就存在着“消极偏向”, 它反映了现代整个心理学领域的价值失衡与导向偏离。自1879 年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心理学就被赋予“三项主要使命:治疗心理疾病; 帮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实完善; 探寻并激发人类的卓越才能”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但二战后, 其重心逐渐偏向心理疾病的评估与矫治, 而忽视了其他两项更为根本的使命。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心理学建立起一套日趋完善的病理体系, DSM-IV 囊括其中的心理病症已经比最初的DSM-I 多出4 倍之多, 现有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也已超过400 多种, 心理学俨然成为一种矫治疾病、消除消极的“类医学”。然而, 回想篇首所提出的“困惑”, 疾病的矫治与消极的消除显然并不能够帮助人类真正摆脱痛苦、谋求幸福。
直至上世纪末, 积极心理学的适时而生重新唤起心理学对人类幸福生活与积极品质的关注。积极心理学将视线聚焦于积极的心理变量和心理健康, 研究领域涉及三个层面:在主观水平上, 关注积极的主观体验; 在个体水平上, 关注积极的人格品质; 在群体水平上, 关注积极的公众品质(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旨在促进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完善和自我实现” (Gable & Haidt, 2005)。积极心理学并不是对传统心理学的彻底批判, 而是一种有益补充与积极完善, “减轻痛苦与增进幸福是两个独立的变量, 完整的心理学应该既是减轻痛苦又是增进幸福的科学”(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
概而观之, 积极心理学与传统认知理论在以下问题上存有鲜明区别。首先, 对心理疾病的理解。认知理论依循医学化的病理模式, 将心理疾病解读为深层障碍与表面症状的结合, 在看待心理疾病的个体时, 唯独看到他们身上可能具有的问题、缺陷、偏差与消极, 全然不顾“自我作为一个复杂合体, 积极与消极的因素完全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体”(Pelham, 1993)。积极心理学则使我们重新理解个体、审视心理疾病。积极心理学认为, 个体与生俱来具有获得幸福的本能和不断成长的潜力; 即使是经历心理疾病的个体, 也有积极的品质与能力, 相比于正常人, 这些积极的品质与能力只是暂时受到抑制。积极心理学并不否认心理疾病中消极变量的存在, 而是主张搁置消极、发掘积极, “积极资源的缺乏独立于消极因素的存在, 同样对心理疾病的产生发挥着作用” (Wichers, Jacobs, Derom, Thiery, & Os, 2007)。基于这一理念, 积极心理学将抑郁解释为积极资源缺乏, 积极的认知“偏差”、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积极的意志行为共同构成积极资源, 致使抑郁的重要原因便是“积极”的匮乏。
其次, 对心理健康的界定。认知理论认为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就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关系, 认知治疗的全部工作都聚焦于缺陷的修复与症状的消除, 以为疾病的免除必然带来健康与适应。然而, “仅仅没有心理疾病并不等于心理健康” (Seligman, 2008), 心理学家Keyes (2005)就曾划分五种心理状态:完全心理健康、趋于心理健康、免于心理疾病、趋于心理疾病, 以及完全心理疾病(Keyes, 2005)。积极心理学家认为, “心理健康并不纯粹是心理疾病等消极因素的免除, 更意味着幸福体验与积极机能的激发”(Seligman, 2008); 同时, 积极的体验与品质又将成为“抵御心理疾病最好的武器”(Seligman, 2008)。积极心理学的这一理念是对传统观点的积极补充, 更为抑郁的干预提供了崭新思路。对于抑郁(或是其他心理疾病), 我们不应着眼于消除症状和弥补缺陷, 更应致力于激发个体的积极潜能, 增强个体的抵御力与适应力。
3.2 积极资源缺乏
由上可知, 积极心理学在解释抑郁时, 有别于传统理论的“消极”视角, 而强调积极因素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在抑郁机制中的作用。
3.2.1 积极认知
不同于认知理论主张的消极认知偏差, 积极心理学认为抑郁的成因在于积极认知的缺乏。这种积极认知体现在正常人身上是一种认知上的“自我欺骗”倾向, 心理学家称之为“积极错觉” (positive illusion)(Taylor & Brown, 1988) 。在现实生活中, 正常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加聪明、更有魅力、人缘更好, 甚至开车技术更好(e.g., Campbell & Fehr, 1990; Taylor & Brown, 1988); 认为自己更有可能经历许多积极事件(例如婚姻美满或是健康长寿), 而不太可能经历消极事件(例如罹患癌症或是发生意外)(e.g., Weinstein & Klein, 1995) 。总结起来, 正常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错觉”:(1)自我提升(self enhancement), 即不切实际地将积极特征归于自己身上; (2) 控制幻想(illusion of control), 即倾向于高估自己对于环境以及结果的控制能力; (3) 不现实的乐观(unrealistic optimism), 即对于自我以及未来抱有脱离现实的积极期待。适度的积极错觉能够提供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对于心理健康大有裨益(e.g., Taylor & Brown, 1988); 而抑郁(尤其轻度忧郁)的产生可能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积极的认知偏差(Haaga & Beck, 1995) 。
3.2.2 积极情感
“从弗洛伊德开始, 心理学家始终认为, 抑郁与幸福、快乐这些积极体验是极端分离的, 即相关为-1.0”(Seligman, 2008) 。但是, 积极心理学家Seligman 在2008 年一篇报告中提出, 抑郁与幸福的相关接近-0.35, 这意味着二者并不完全抵触, 抑郁的发生常与幸福的贫乏共存。具体而言, 积极心理学家将幸福体验解构为三种成分(Seligman, 2002a):(1) 愉悦感(pleasure), 包含三类积极情绪, 即指向过去的积极情绪(满足、坦荡、自豪等)、指向未来的积极情绪(乐观、希望、信念等), 指向现在的积极情绪(此时此地的快乐体验); (2) 参与感(engagement), 是指对一切生活事件的高度投入以及因此萌生的内心充盈的积极情感; (3) 意义感(meaning), 是指将自己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结, 精神自我得以延展升华的积极情感。研究数据表明, 这三种细化的幸福体验也与抑郁有着密切关系, 例如, Seligman 等(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报告, 临床抑郁病患的愉悦感、参与感与愉悦感水平均显著低于非抑郁精神病患与正常被试。
积极情感贫乏与抑郁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仅是方向模糊的相关关系, 还是前后相继的因果关系?积极心理学家认为, 抑郁个体常表现出愉悦感、参与感及意义感的缺乏, “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抑郁的症状表现之一, 但是, 它很可能是导致抑郁的真正原因”(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这种解释源于积极情感本身具有的扩展与建构(broaden-and-build) 的适应功能。一般认为, 消极情感通过缩小个体即时的认知和行为系统, 在危急状况下帮助个体迅速组织应激资源, 以免自身受到侵害; 正好相反, 积极情感却能扩展个体即时的认知和行为系统, 促使个体突破限制、开放经验, 进而建构起持久的心理资源, 个体主观的适应状态(well-being) 最终将会处于螺旋上升的发展序列上(Fredrickson & Joiner, 2002) 。积极心理学家相信, 正是由于积极情感贫乏使得个体无法建构起持续的发展资源, 从而导致抑郁。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路径存在的可能, 例如, Wichers 等(Wichers, Jacobs, Derom, Thiery, & Os, 2007) 采用双生子研究范式, 发现对于既定的抑郁遗传因子, 更多经历积极情感可以有效降低抑郁发病风险, 这从行为遗传角度为积极情感贫乏先决于抑郁发生提供了佐证。
3.2.3 积极行动
积极心理学认为, 积极情感可以借助某些行为或活动来主动诱发; 抑郁个体在积极情感上的缺乏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这些“积极行动”上的缺乏。积极行动可以是各个生活领域中各种性质的活动, 它可以是行为性的(例如有规律的锻炼身体)、认知性的(例如经常性的感恩祷告), 意志性的(volitional)( 例如为达成目标而努力奋斗)。积极行动可以长时间地促进积极情感; 尤为重要的是, 由行动产生的积极情感, 相比环境改善(例如彩票中奖)带来的积极情感, “适应效应”(adaptation effect)* 要小得多(Lyubomirsky, Sheldon, & Schkade, 2005) 。对于抑郁个体, 积极行动的缺少一方面导致其积极情感的贫乏, 另一方面又使适应效应在他们身上的影响更为突出, 使其更易长久沉浸于消极事件或消极情感的影响之中, 这种双重作用无疑制造出情感的恶性循环。
积极行动缺乏可能导致抑郁, 该假设还能在积极心理学关于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 的研究中得到验证。Peterson 与Seligman (2001, 2004) 的“ 行动价值分类体系”(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of strength) 总结提炼了个体性格中24 种优势, 这一体系与“积极情感的扩展建构理论”被认为是积极心理学发展至今最具影响的两大成就(Lopez et al., 2006) 。Seligman 等(e.g., 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认为, 每个个体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系列优势, 如果能在每天的生活中运用这些优势, 将会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体的参与感与意义感。即使抑郁个体, 也有自己的显著优势; 抑郁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身上积极品质的彻底缺位, 而只是这些积极力量未被充分运用发挥, 这种行动的缺乏使其失去了增进积极情感、建构心理资源的机会。
4 积极心理治疗及实践
在积极心理理念下发展起来的积极心理治疗(positive psychotherapy, PPT), 相比认知治疗, 工作重点不在于矫治消极偏差、减轻抑郁症状, 而在于增进积极情感、激发性格优势。积极心理治疗看似有意“忽视”抑郁个体的消极症状, 实际上是通过直接建立个体自身的积极资源来对抗症状、治疗抑郁。表1 粗略列出积极心理治疗最为常用的一些技术, 它们均被证明能够显著提升积极情感、缓解抑郁症状(e.g., Giffen & Zhivotovskaya, 2007; 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从这些技术中不难发现, 积极心理治疗的工作机制似乎是外在的、行为的, 然而, 对于个体性格优势与积极资源的强调, 是它区别于行为治疗以及以往任何疗法的本质所在。
表1 积极心理治疗技术
| 练习 | 描述 |
| 运用优势 (using strengths) | 借助“优势行动价值调查”(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 VIA-IS: Peterson & Seligman,2001), 评估个体的“显著优势”(signature strength), 提供运用优势的活动建议。 |
| 记录幸运 (counting blessings) | 每晚入睡之前, 写下三件以往任何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值得欣喜的事情, 并且思考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的可能原因。 |
| 实践感恩 (gratitude visit) | 想想你是否对某人抱有感激, 但却从未向他/她郑重地表达过这种情感。如果这样, 请你用心地写一封感谢的书信; 并且尽可能地将这封信当面念给他/她听。 |
| 编写自传 (biography/tribute) | 想象你已历经一段丰富精彩的人生旅程, 你的生命就此结束。请你写下1 至2 页的自传, 尝试发现你希望成为的自己, 包括具备的品质、取得的成就、珍惜的事物, 等。 |
| 学会体味 (savoring) | 想想你是否对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从不经心, 常常以敷衍的态度匆忙了事(例如吃饭)。请你尝试放慢生活步调, 享受这些生活细节中的乐趣; 并且记录这种感受, 将其与之前的感受相比较。 |
目前, 已有不少关于积极心理治疗干预抑郁的效果研究。其中, 干预的形式既有个体治疗也* 所谓“适应效应”, 是指个体对于积极事件或积极情感的适应倾向, 消极事件或是消极情感对于个体的影响更为弥漫、更为持久。个体会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理所当然, 而对坏事则纠缠不放。这一现象已为众多研究证明, Baumeister 等人(2001) 曾对此进行过翔实的综述(见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Finkenauer, C., & Vohs, K. D. (2001).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4), 323-370) 。有团体指导, 干预的对象既有轻中度抑郁个体也有符合临床诊断的严重抑郁患者(e.g., 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 Seligman, 2002b) 。这些干预研究证明, 积极心理治疗:(1) 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消除症状、减轻抑郁; (2) 更能发挥个体的性格优势, 提升个体的积极情感; (3) 还能有效降低抑郁复发的风险, 建立抵御心理疾病的预防机制。近来, Seligman (2008) 又建构了“ 积极健康”(positive health) 的概念, 认为积极健康是个体在生理上(biological) 、主观上(subjective)、机能上(functional) 都能表现极佳的状态。生理健康是指没有严重生理疾病, 同时基本生理机能良好。主观健康涉及个体的主观体验, 包括以下状态:(1)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积极感受, 例如有活力、有能量; (2) 乐观, 即指向未来的积极感受; (3) 高生活满意度; (4) 积极的情绪, 它不仅指消极情绪的最小化, 更意味着对于生活的参与感、意义感。机能健康则是个体对于生活具有良好的适应。Seligman (2008) 认为, 积极心理治疗可以有效实现积极健康。
综上所述, 积极心理治疗作为一种证实有效的干预手段, 为抑郁的治疗展现了新的希望。但是, 正如积极心理学家所强调的, 积极心理治疗并不是对传统心理疗法的否定与颠覆, 而是对它的补充与完善, 二者的相互整合、共同作用将会是心理治疗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人提出, 内观冥想(mindfulness) 是积极心理治疗与认知治疗融合的契机(Hamilton, Kitzman & Guyotte, 2006), 这类研究就是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冯正直, 张大均. (2005). 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14, 103–105.
乔纳森·布朗 (著). 陈浩莺等 (译). (2004). 自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美国医学会 (编). 刘琼, 周瑞(译). (2008). 轻松告别抑郁症.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任俊. (2006). 积极心理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Abramson, L. Y., Metalsky, G. I., & Alloy, L. B. (1989). Hopel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358–372.
Alloy, L. B., & Abramson, L. Y. (1979). Judgment of contingency in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students: sadder but wis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08, 441–485.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Finkenauer, C., & Vohs, K.
D. (2001).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323–370. Beck, A. T., & Weishaar, M. E. (2000). Cognitive therapy. In
R. J. Corsini & D. Wedding (Eds.), Current psychotherapies (pp. 241–272). Itasca, IL: F.E. Peacock. Campbell, J. D., & Fehr, B. (1990). Self-esteem and perceptions of conveyed impressions: is negative affectivity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real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122–133.
Fredrickson, B. L., & Joiner, T. (2002). Positive emotions trigger upward spirals toward emotion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 172–175.
Follette, V. M., & Jacobson, N. S. (1987). Importance of attributions as a predictor of how people cope with fail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205–1211.
Gable, S. L., & Haidt, J. (2005). What (and why) is positive psycholog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9, 103–110.
Giffen, D., & Zhivotovskaya, E. (2007). Positive psychology toolkit for coaches: book proposal.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aaga, D. A. F., & Beck, A. T. (1995). Perspectives on depressive realism: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ve theory of depres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 (1), 41–48.
Hamilton, N. A., Kitzman, H., & Guyotte, S. (2006). Enhancing health and emotion: mindfulness as a missing link between cognitive therapy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 (2), 123–134.
Ingram, R. E., Miranda, J., & Segal, Z. (2005).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In L. B. Alloy & J. H. Riskind (Eds.),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emotional disorders (pp. 63–92). Florence: Routledge. Keyes, C. L. M. (2005). Mental illness and/or mental health? Investigating axioms of the complete state model of health.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3, 539–548.
Lewinsohn, P. M., & Essau, C. A. (2002).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In C. L. Hammen & I. H. Gotlib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pp. 541–55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Lopez, S. J., Magyar-Moe, J. L., Petersen, S. E., Ryder, J. A., Krieshok, T. S., O’Byrne, K. K., Lichtenberg, J. W., & Fry,
N. A. (2006). Counseling psychology’s focus on positive aspects of human functioning.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4, 205–227. Lyubomirsky, S., Sheldon, K. M., & Schkade, D. (2005). Pursuing happiness: the architectures of sustainable chang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9 (2), 111–131.
McKendree-Smith, N., & Scogin, F. (2000). Depressive realism: effects of depression severity and interpretation tim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6 (12), 1601–1608.
Monroe, S. M., & Simons, A. D. (1991). Diathesis-stress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life stress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ressive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 (3), 406–425.
Pelham, B. W. (1993). On the highly positive thoughts of the highly depressed. In R. F. Baumeister (Eds.), Self-esteem: The puzzle of low self-regard (pp. 183–199). New York: Plenum Press.
上一篇: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进展
推荐阅读